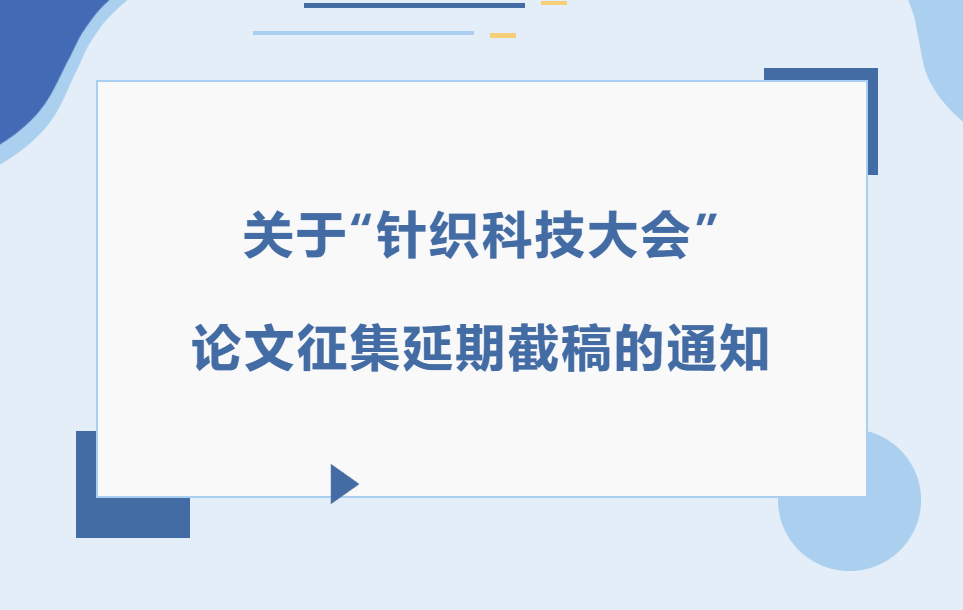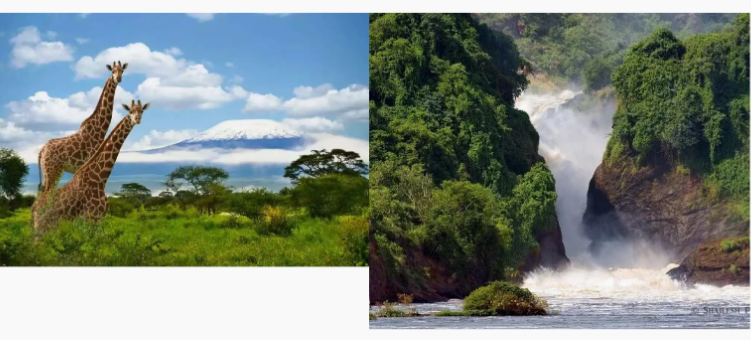会员登陆:
巴里·艾肯格林:从英国工业化能学到什么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站在了十字路口。它的最新增长记录是惊人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媲美。但中国经济失衡同样惊人。中国的产出增长是用投资整整一半的GDP来维持的,尽管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投资还能保证生产率。家庭消费只有GDP的三分之一,而一般经济体要占到三分之二。
与如此低水平的消费相伴而生的,是日益恶化的不平衡--既存在于城乡之间,也存在于精英和大众之间。心高气傲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中意的白领工作,又不愿意接受蓝领职位。
中国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他们需要实现经济从投资到消费的再平衡,也认识到这意味着发展可以提供白领岗位的服务部门。他们还明白需要建立社会安全网、强化农村产权。
但中国官员担心从投资到消费以及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意味着增长减速。扩张生产率尚低的服务部门会拖累总产出。而如果增长进一步减速--年增长率已从10%降至7.5%--社会动荡可能会加剧。
那么,中国领导人应着眼于何处应对这些挑战呢?
看似不可能的是,他们可以从英国找到指南。正如中国的工业化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保持每年10%以上的增长,200年前英国的工业化也是前无古人的。
当然,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故乡。其经济增长比当时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快。
但英国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不平等性日益加剧,直至最近还有所谓的“生活水平争论”的学术问题。家庭产权保护极为不力,发生了所谓的“圈地运动”。此外还有关于城市污染和不人道的工厂环境的抱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称之为“黑暗作坊”。
不可避免地,英国爆发了社会动荡。比如因19世纪初纺织业机械化而起、摧毁新技术的卢德派和工人摧毁打谷机的施荣暴动(Swing Riots)。
英国政治家的应对措施是改革社会安全网。1834年,《新济贫法》(New Poor Law)规定了社会福利的国家标准。尽管争议重重,但穷人仍可以获得补助而不必进入压抑的救济所。另一个方案,即所谓的户外救济(outdoor relief)也获得了扩大,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成本最低的方法。
其次,随政治改革到来的还有旨在再平衡经济的政策变化。1846年,《谷物法》被废,这拯救了衰落的农业部门,促进了结构转变,先是转向了制造业,后来又转向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
最后,英国政治家并没有寻求维持该国世界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地位。诚然,当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时,他们受到了批评。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抵挡经济从农业进步到工业再进步到服务业的自然演化,而是成功地让英国获得了整整一百年的持续经济增长。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
行业热点 TOP10
.mor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65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659号Copyright 2010 www.ckia.org inc.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